油麻地镇的男女老少都在兴冲冲地走动着,谁也不是空手。wPP文惺网
整个油麻地,只有两户人家没有参加这场史无前例的、群情激荡的“拿回”,一是邱半村家,一是杜少岩、杜元潮父子。wPP文惺网
邱半村早在两个月前就已倾家荡产,只剩下一幢空无一物的大屋。这些日子,他和家人很少在镇上露面,只是关紧了门,躲在门后,紧张不安地听着外面的动静。当邱子东挣扎着要往外面跑时,邱半村就用已经半身不遂的身体死死挡在门口,用含糊不清的言词喝令邱子东老老实实地在家呆着。wPP文惺网
杜少岩与杜元潮在人们如狼似虎地出入程家大院时,父子俩一直手牵着手,在不远处的一棵枫树下无声地站着。wPP文惺网
在他们父子面前经过的人,会有一两个人提醒道:“一根桩!愣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赶紧地去取一两件东西!”wPP文惺网
杜少岩、杜元潮依然站着不动。wPP文惺网
那张黄梨木六柱式架子床被人抬走了,那条红木夹头榫长案被人抬走了……wPP文惺网
杜元潮几次要冲上去干什么,都被杜少岩用有力的大手死死抓住了。wPP文惺网
杜元潮站在父亲身边,心里想着的是要进程家大院。自从他和父亲离开程家大院后,他就再也没有跨进过这座大院的大门。他不是想看院子,也不是想看那些人是怎样将程家大院的东西抓到自己手上的,他想知道此时此刻采芹在哪儿、采芹怎么样了。他似乎看到了她在恐惧中哆嗦,像一只从冰水中挣扎出来的鸽子。wPP文惺网
杜少岩似乎看出了儿子的心思,拍拍他的脑袋安慰他:“没有人会欺侮一个孩子的。”wPP文惺网
杜元潮的眼睛里便有了亮晶晶的泪水。wPP文惺网
油麻地的男女老少还在走动,一个个喜气洋洋。wPP文惺网
这是油麻地的节日———不是节日的节日,盛大的节日。wPP文惺网
但,李长望发怒了,当他带着他的队伍与工作组成员从场院赶到程家大院时,程家大院已是空空荡荡。wPP文惺网
“是分浮财,是他妈分,不是他妈抢!”他爬上镇上那座高塔,用一只铁皮喇叭向四周叫喊着:“将所有从程家大院取出的东西,给我统统送到场院里,然后统一分配,谁胆敢不服从老子的命令,谁胆敢私自窝藏,一旦发现,绝不轻饶!”说完,从腰间掏出手枪,往空中叭叭叭打出去一梭子子弹。在塔下站着的那几个兵,也端起枪,呼应着,朝空中射出震慑人心的子弹。wPP文惺网
人们嘟囔着,但却乖乖地将那些东西又从家中搬到镇中心的大场院里。wPP文惺网
这些大大小小的东西,在程家大院里,各自在各自应呆的地方呆着,倒也不显有多么的多,现在一旦散乱地平铺开,差不多摆满了一场院,看上去竟然有一望无际的感觉。wPP文惺网
分配是公平合理的,有根据的,都可以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的。wPP文惺网
轮到杜少岩、杜元潮了。工作组说:“你们可以先自选。”wPP文惺网
杜元潮的眼睛一直盯着那张床。wPP文惺网
杜少岩从儿子的目光里得知了他的心思:“那床不是我们这样的人睡的,还不如要一只盛水的桶,一张吃饭的小桌子。”wPP文惺网
但杜元潮的眼睛里只有那张床。一个孩子竟然对那么多东西视而不见,视野里只有那张床,这未免有点儿可笑。但不知为什么,杜元潮就只想要那张床。wPP文惺网
杜少岩叹息了一声,决定满足杜元潮的愿望,用手一指,向工作组说:“这孩子,想要那张床。”wPP文惺网
工作组组长将杜少岩拉到了一边,与杜少岩嘀咕了一阵,杜少岩连连点头,转身走向杜元潮,说:“那床别人要下了,你另选一件吧。”wPP文惺网
“谁……谁要了?”wPP文惺网
“你就别问了,快点说,除了那张床,你想选哪一件?”wPP文惺网
“哪一件也……也不要了!”杜元潮说罢,扭头就走。wPP文惺网
杜少岩一把抓住杜元潮的胳膊:“儿子,还是选一件吧。”wPP文惺网
当杜元潮向那一场院的东西望去时,发现了那张他与采芹一起读书写字的长案还在那儿,又有了笑脸:“要……要那张长……长条桌吧。”wPP文惺网
“净选一些没有用的东西。”杜少岩一边抱怨着,一边走过去,拉起了那张被雨水洗得镜子一般明亮的长案……wPP文惺网
工作组撤了,李长望的队伍也撤了,但李长望却留了下来。当上头问他“你是留下还是走”时,他毫不犹豫地说:“我留下。”他脱掉了那套破旧的军装,交出了那支驳壳枪,从部队转入地方,成为油麻地镇的最高行政长官。wPP文惺网
程家大院成了镇委会的办公处,在为他建造的房子还未落成之前,程家大院内一侧厢房成了他临时的居所。wPP文惺网
程瑶田一家,被赶到后院,住到了杜家父子当年住的那幢房子里。自从杜家父子搬出后,那幢房子又像以往一样一直空着,当程瑶田吱呀推开木板几乎朽烂了的门时,一股潮湿的带着浓重霉味的气流扑面而来,几乎使他晕倒。一家人试探着走进屋里很长一阵时间之后,才慢慢适应屋中昏暗的光线。他们在屋里慢慢地走着,像走进了一个岩洞,只有过去常来这屋里找杜元潮玩耍的采芹显得轻车熟路,在屋里很熟悉地从这个房间走进那个房间。当采芹的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撩着不时地粘到她头发与脸上的蜘蛛网时,禁不住小声啜泣起来。wPP文惺网
程瑶田却说:“蛮好的一幢房子。”wPP文惺网
没有佣人,没有长工,贴身的管家范烟户,也不再见到,听说他一手抓了一把石灰,撒向双眼,将双眼呛瞎了。wPP文惺网
一片孤寂。wPP文惺网
采芹已深刻地感受到了油麻地的巨变。外面的世界似乎沉浸在无比的欢愉之中,总能听到鞭炮声、锣鼓声、喧闹声。而所有这些声音都会给这个小女孩带来不安与恐惧。她整天跟随着母亲,一旦发现母亲不在自己的身边时,就会大声尖叫,如在噩梦中突然惊醒一般。她的眼睛要么睁得大大的,要么就扑在母亲怀中紧紧闭上。母亲不时地轻拍她的后背:“芹儿,别怕,芹儿,别怕……”有时,他们会听到一些消息:东王庄的大地主陆平沙被镇压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进去的,脑浆流满一地;黄家荡的一个土匪头子被士兵抓住了,用铡草的铡刀活生生地切下了脑袋……虽在夏日,但每逢听到这些消息,全家人却感觉到冥色四合、寒风瑟瑟。wPP文惺网
程瑶田依旧穿得一尘不染,但身体已瘦弱不堪,立起时犹如一根竹竿挑起一套衣服。他常站在门口眺望天空。这年的夏天,总是有雨,雨打枫树,点点滴滴,总有一番清冷。天上很少见到太阳,阴沉沉的,叫人胸闷,叫人心虚,叫人感到无望。wPP文惺网
房屋不再是他的房屋,田地不再是他的田地,但他觉得,事情正如这没完没了的雨水,还没有结束。wPP文惺网
采芹总是呆在新的家中,与母亲终日厮守,不肯出门一步。有时候,她会坐在窗前,去想念田野、风车、木船与水牛,更想念杜元潮与邱子东。杜元潮、邱子东,邱子东、杜元潮,他们两个是被轮番想念的,不过想念得更多的是杜元潮。一番想念之后,往往是一番悲伤。她忽然地觉得,他们与她生分了———整个世界都与她生分了,就她独自一人了。这种感觉是两年前她与杜元潮在田野上玩耍,然后走失了,环顾四周只见田野茫茫空无一人时的感觉。如果母亲这时不在她身边,她就会自己将自己抱得紧紧的。wPP文惺网
杜元潮敲开了邱子东家的门。wPP文惺网
邱子东一见杜元潮,立即跑了出来。wPP文惺网
杜元潮什么也没说,头里走了。wPP文惺网
“去哪儿?”邱子东跟在他身后问。wPP文惺网
杜元潮只顾往前走着。wPP文惺网
杜元潮口吃,本来说话就少,而一旦见到邱子东,就会更加口吃,因此,他在邱子东面前能不说话就不说话。特别使他灰心的是,邱子东长了一张特别会说话的好嘴,唧唧呱呱,一路畅通,流利无比,而他呢,是个结巴,越结巴就越结巴,到了极处,竟脸红脖子粗,半天才好不容易吐出一个字来,像被人双手死死掐住了脖子一般,又好像是刚从冰窟窿中被人救起似的。若是一时无法避开邱子东,那么,他永远是低头蹲在地上,或是默默地呆在角落上。那时,他的脑袋里空空的,却又涨涨的,十分的沉重。偶尔,他会抬起头来看一眼邱子东,十有八九,他见到的邱子东,都是头微微上扬,一副傲慢、目中无人的样子。邱家崩排后,邱大少爷邱子东,蔫了许多,但在杜元潮面前,他骨子里却还是邱大少爷。wPP文惺网
邱子东紧追几步,走到杜元潮并排的位置上:“是去看采芹吗?”wPP文惺网
杜元潮仍不作答。wPP文惺网
采芹家的门关着。wPP文惺网
他们屋前屋后地转着,可就是不见采芹开门走出来。wPP文惺网
邱子东说:“我们唱歌吧,她听见了,就会出来的。”说罢,咽了咽唾沫,唱了起来:wPP文惺网
大秃得病二秃慌,三秃在家熬药汤。wPP文惺网
四秃去取药,五秃去报丧。wPP文惺网
六秃去打墓,七秃抬,八秃埋,九秃从南哭上来。wPP文惺网
我问九秃哭甚的,“俺家死个秃乖乖!”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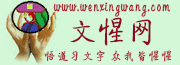

 | | 微信公众号
| | 微信公众号  | | 站长微信
| | 站长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