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这个词我们并不陌生,至于它的含义一般具有点文学常识的人似乎也懂,但真正要给诗下个定义,我就觉得不是那么简单了。五十年前我曾和一个朋友探讨过,他说有韵律、字句整齐就是诗。我说依老兄之见,“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诸卫,蒋沈韩杨”也是诗啰,这显然不是。他继而补充说道还要表达一定的思想内容。我觉得也不大对,“天生物,人最灵。根本坏,何为人?教弟子,先明伦。行有余,始学文”,这符合你说的条件,但自古以来就没有人把《三字经》和《三字幼仪》之类看成诗。那时我们接触新诗极少,谈诗都把它忽略了。
前几天有个年轻人问我什么叫诗,不知如何回答。我去查了一下字典辞书,说法也不一。
“有韵律可歌吟者的一种文体。”这是《辞源》上的解释。现在不少新诗就很淡漠韵律,《辞源》之说,似乎包括不了一些新诗。
“文学的一种体裁。文学的重要类别之一。”《辞海》这种解释太笼统,于是它叫参看“诗歌”的解释。对诗歌的解释是:“文学的一大类别。它高度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饱和着作者丰富的思想和情感,富于想象,语言凝练而形象性强,具有节奏韵律,一般分行排列。”这是对诗歌的解释。问题说诗,诗和歌有区别没有呢?似乎又说开了点。而且有的新诗就不讲究节奏和韵律,至少它的节奏和韵律不强,这样的解释似乎也没把当今所说的新诗包罗完。
《中文大辞典》上说“有声韵可歌吟之文谓之诗。古诗多四言,其后五言、六言、七言等相继而起,至唐乃有古体近体之分。现代更有所谓新诗,或模仿西洋诗,或自创新体,以语体文出之,或用韵或不用韵,形式亦非若旧诗之整齐。”《中文大辞典》是台湾出版的,此说代表台湾学界的解释。第一句是对诗下的定义,觉得没包括新诗,因而接着加以补充。从补充谈到新诗有四点:其一,新诗来源,模仿西洋诗或自创新体;其二,语体出之,就是用白话;其三,可用韵可不用韵;其四,句式长短不一。
有声韵可歌咏之文谓之诗。这个给诗下的定义很明显包括不了新诗,所以只好在诗的定义之外加说明。这就说明要简单给诗下个定义很难。
谈到诗就不得不要说一下新诗了。新诗模仿西洋诗之说,我认为不太准确。无论哪种语言写成的诗,就一定符合那种民族语言的特定文学形式------诗;它既然是诗就肯定与散文有别。我记得我读高中时,俄语教本上有一篇课文是首诗,内容大意是除夕的十二点新年快到了,新的一年就要替换旧的一年,如像哨兵换岗一样。用俄语朗诵起来既有节奏也有韵律,而且句式也比较整齐。俄语的散文和俄语的诗就是有区别。老师叫我们翻译,我说别人的作品是诗,我们用汉语来翻译就应该译成符合汉语的诗。若用散文句式去翻译就把别人的原作诗散文化了,变了味了。当时班上翻译的人有七八个,多是用白话散文句式翻译,真是五花八门。我读过几年私塾,略知平仄,学着把它翻译成一首五言绝句:“午夜新春至,钟鸣十二时。值班如哨卒,换守莫迟迟。”得到俄语老师的好评。
有年我校外语系有个教师,他正在讲授一首英语诗。他自己觉得用白话翻译出来不够味,请我帮他用诗来翻译。我给他翻译成一首七言诗。他读了高兴地说道:“对啰对啰,这下就对啰。”由此我觉得所谓模仿西洋诗,实际是模仿用汉语白话散文翻译过来的西洋诗。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别喝生水,要喝开水”,原诗用俄语写成符合俄语那种民族形式的诗,用汉语这样翻译出来实际就变味了,是散文句式了,但原作是诗。我们模仿这样的诗,是模仿经过翻译变了味的西洋诗了。
至于自己创作的新诗,那就随心所欲,个人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这也是我说的新诗易写的原因。我在中文系管事时,有一个军人诗人,某报刊登过艾青接见他时的照片。他曾持此照片的复印件来找我,和我谈起诗来。后来学生组织请他作报告,谈他创作诗的体会,他说:“写散文极难,写诗最容易。写诗关键要掌握词汇,词汇越丰富,就好写诗。我奉劝诸位想方设法买本《辞海》。有了本《辞海》,保险能写好诗。高山,大海;巍峨,澎湃。这就四个词,组成诗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要说这四句诗有多好就有多好。俯首,低眉;静色,黄昏。像这样把词放在一起,也就成诗了。”
这位战士说的诗,在他看来就是选择一些词凑在一起,形成似通不通的语句,再把它分开排列,就成诗了。我自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讲完,我请人引他去休息室吸烟喝茶,我还得唱点反调,给学生讲一阵子。
此后无论是《诗刊》还是四川的《星星》每期我要翻来看看。有些诗朦胧晦涩,让读者自己去领会,至于语言我也尽量去领会其美处,想培养点写新诗的情趣,偶尔也写写,但总觉得不是味儿。我不是赶时髦,而是觉得文体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更新的。诗体也应是如此。
新诗的定义不好下,自然评价新诗的标准也就难说。一首新诗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比较不好把握。1986年我去成都出差,有天去省文联,有意和《星星》编辑部的朋友开了个玩笑。我胡凑了几句,另外抄录了该刊两年前刊载过的一首。我将两页诗笺给他们看,我胡凑那首我假托闻捷写的;他们曾发在《星星》上那首我说是一个二年级的学生写的。他们说闻捷真是写新诗的老手,说了一箩筐好话。他们曾发表过的自己毫无印象了,却说“那是什么诗啊”。我笑着把真相告诉他们,他们也觉得好笑。他们中有个是我的校友,应该是我的师兄,他说新诗这玩意儿很难评价,我们的刊物是以刊新诗为主,很少刊载旧体。有年张秀熟老的旧体诗,刊发时被删改了一下,后来张老大发脾气,说给他改了就不合格律了,编辑部只好向他道歉。我们发表新诗一是看作者在其他刊物发表过没有,名气大的来搞照登。新手之作,就凭编辑部的感觉了。
新诗难以在群众中流传,解放前的姑且不说,解放后六十几年出版的新诗诗集也不少,至于报刊登载过的新诗就更多了。我过去兼任南充市文联副主席时,曾作过一次简单的调查,问过一些文化人,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背诵一首新诗,能记得诗的题目的也寥寥无几。我读大学时严尚志先生讲闻捷的长诗“东风吹动黄河浪”,花了几个学时,原诗我们一句也记不得,只记得一个题目。傅先生讲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大家只记得捏一个你来捏一个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为什么会这样?不少新诗(我不是说的全部),语言晦涩,诗句意思跳跃性太大,内在联系过于松弛,既不好读,更不好记。倒是那些音韵铿锵,带有点节奏的新诗,读起来比较上口。六十三年前我读初中时,课本上选了梁启超的《志未酬》,当年语文教师要求背诵,至今我基本上还能记得。这首诗语意连贯,内在联系强,这是好记的主要原因。
新诗写好不容易,要想写新诗出名,难!除非有人吹。如果连散文都写不通顺,就去写诗,那就是“犹未能操刀而学割也”。年轻人若连文章都写不通顺,就去致力于写诗尤其是写新诗,那就误入歧途啦!
2006年我与拙荆去银厂沟避暑回家十二天,她就病了,经检查是白血病,百般医治,终无良效,第二年三月不幸与世长辞。她去世一周年我写一首小词,寄调《唐多令》。
“避暑去远方,回家上病房。突然间,倍感凄凉。灯下诉情情未了,卿去也,我心伤。
孤独起彷徨,常忆旧时光。耳畔低声常嘱咐:天气凉,加衣裳。”
有个青年朋友看见了,说是新诗。我告诉他这是词。不能因为是语体就以为是白话诗。我六零年暑假回家,看见家乡蓬蒿遍野,满目荒凉,无数乡亲死于饥饿。我写过一首自度曲,现录于此。
离家不到两年,归来不见旧时颜。新坟旧冢,歇土荒田,断壁颓垣,井上青苔长满。荒山树木少,
乡镇无人赶。村头巷尾,多见老年少年,一个个,枯瘦浮肿,蓬头垢面,身着破衣衫。问起家常事,
摇头摆手,泪流满面。谁之过?发指对苍天!
做为一个门外人,我认为新诗易写写好难。我觉得不管是那种诗体,应该让群众看了或听了能明白它的意思。新诗虽然是语体,如果内容晦涩,使人看了或听了不知所云,那就有失写诗的意义了。我很少写诗,也写不好诗,老了没事想学。写这篇小文,一是告诫年轻朋友若你爱好文艺,先好好练习写文章,练好基础功夫,再学习写诗。若没有写作的基本功就去写所谓新诗,就会把自己误了。二是想抛砖引玉,以冀得到内行先生女士的帮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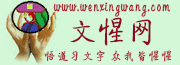

 | | 微信公众号
| | 微信公众号  | | 站长微信
| | 站长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