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对诗的纪念。诗歌写作本身是纪念性的,既对于往昔的诗歌,也对于匆匆岁月。诗人似乎怀有让时间停止的梦想,或者可以说,诗人通过严肃的写作与时间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游戏,直到某一天发现头发斑白了。由于这一小群人对世界的爱的固执,他们的精神贡品有朝一日会成为新的纪念物。kTk文惺网
三种时间中的过去时间并未完全逝去,它在我们的记忆中若隐若现,以回声的方式作用于我们,记忆者的回忆就是返回并抵达那个泉水丰沛的神秘地带,中国先哲将它命名为“泪谷”,希腊人称之莫涅摩辛涅(Mnemosyne)与厉司(Lethe):记忆之泉与忘川。记忆或遗忘皆难解之谜,传说古希腊的求神降示者必须喝这两条山泉的水。博尔赫斯曾写下一句奇怪的诗:不存在的事物只有一件,那就是遗忘。为什么说遗忘是不存在的呢?或许因为人本质上总是不停地在回忆,在缅怀。诗人的怀旧式情感如此浩大,以致于必须发明出“万古愁”这个词来承载。我想,所谓宇宙灵魂、天地之心所指都是同一个东西,它收留并保管着我们个人的记忆。
来自生存的和精神的双重危机,考验着当代诗人的勇气和耐心,他在心中呼唤着“作为内在凝思和经验保存”的记忆王国(一个并不存在的国家)的降临,作为此呼唤的应答,记忆女神摇身成为他的保护神,道路之神经常给予他引导。
处于悬空状态的精神必须重新赢得栖居之地,而写作,正如阿多诺所说,将成为此栖居之地。一方面是本土经验的内在记忆化,一方面是诗歌地理空间的拓展与陌生化的持续需要,经验的主人感受到断裂和新的撞击;记忆者意识到自己是母语的携带者。写作,倘若未曾认清母语的遗产,就有可能再度落空。
精神的缺席可以这样来理解:一个被耽延的尚未现身的“现在”遮蔽在不准确的写作行为中。诗人的词语是时间和生命的混合物,对于精神与历史及时代的关联,我尚未找到比招魂术这个词更贴切的比喻,诗人的漫游或许有可能获得破译不同文化语符的仪式道具,而写作者文化身份的重新确认,则几乎是一种自招其魂的开始。
处于崇尚物质主义的、灵肉分离的时代,诗更其作为挽歌——对逝者,对曾经有过的精神完整性的招魂。诗是挽歌,所以诗歌艺术是一种招魂术。《易》有游魂、归魂之卦象,可作万物之灵皆合于阴阳变化解;《楚辞·招魂》本于楚地的民间习俗,而招魂仪式在一些南方省份至今犹存。司马迁描述此习俗时认为是生者对临死状态的人所作的挽歌:“精神越散,与形离别,恐命将终,所行不遂,故愤然大招其魂。”《招魂》诗中的主体巫阳无疑堪与希腊神话人物俄尔甫斯相媲美,属于原创诗学意义上的中国诗人原型,她对着冥界歌唱,招唤死者返回,将语言化作无限凄美的祈祷,亦是通灵者的一种越界的对话。
另一种唱给自己的挽歌,同属有关终极事物的最后的言说,与“先行到死亡中去”的存在主义诗学不谋而合,将死亡事件引向天人之际,可以说是招魂诗的变体。
当代诗因太多的否定因素,常常如燕卜逊所说:“不过是一场鬼脸游戏”,或许是时代本身的否定因素使然。语言的接力据说发生在三五年之间,三五年为一变。我不置可否,但乐观其成。然我终不是文学史家,就当下而言,没有极深研几的识力无从谈变化。语言的变化绵延不尽,与世代相颉颃,“变风发乎情”这一儒家诗学言说虽古拙,却并未过时,诗人之情通乎世情,世情所迫,“诗变”乃不得已而发生。如此演绎虽只是常识的重申,亦可理解为从常识出发的一种敦促。然“天不变,道亦不变”,诗歌不会因形式的变迁而放弃对心灵守护神的召唤。
为了更好地纪念诗歌这种久远的文学类型,一种对重返精神原乡的诗歌写作的期待,已然要求诗人们超越日常生活的散漫无序,同时避免过度的精致化,在个人记事中观照历史,又从历史诗学中参透现代感性;不是带着恋尸癖般回首的遗憾,而是将“原始灵视”(荣格语)的修为当作朝向终极性之一瞥的日课。那么,避免毁宗庙之事重演的当代忧虑或将帮助我们度过更大的危机。“人心维危,道心维微”,深于诗者,其见天地之纯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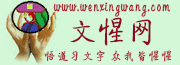

 | | 微信公众号
| | 微信公众号  | | 站长微信
| | 站长微信 